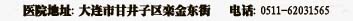上海国际会议中心
OCAP·精彩回顾
Kharasch教授:手术,疼痛与麻醉转归EvanD.Kharasch教授
《麻醉学》(Anesthesiology)主编
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麻醉学教授
麻醉转归需考虑的因素不同,年轻患者主要在于疼痛、神经毒性及发育影响,中年患者主要包括疼痛、恶心呕吐、副作用、术中知晓及能否及时恢复工作,老年患者则包括疼痛、谵妄、记忆/认知障碍、心肌梗死、卒中、自理能力及生存率。急慢性术后疼痛面对使用阿片类药物与引起术后呼吸抑制的两难,引起诸多挑战。
挑战1:有效镇痛
超过80%患者表示术后疼痛未得到有效缓解,这一局面在近20年并无有效改善,术后急性痛是术后慢性痛的主要危险因素。年《疼痛学杂志》(TheJournalofPain)发布的《术后疼痛的管理指南》指出,术后超过80%患者存在急性术后痛,其中近75%表现为中到重度、甚至极重度疼痛,术后疼痛得到有效缓解者不到半数,控制不佳的疼痛可影响患者的生存质量、器官功能及其恢复、术后并发症发病率,以及术后持续性疼痛的风险。年发表于《欧洲麻醉学杂志》(EuropeanJournalofAnaesthesiology)的研究对例住院患者分析发现,术后痛(尤其是中大型手术后)的处理并不令人满意。术后慢性痛的分析表明,90%疼痛分布于切口疤痕周围,26%在疤痕范围内;其疼痛可描述为酸痛(61%)、麻木(52%)、刺痛(31%)、紧缩感(29%)、异常性疼痛(25%)、压痛(12%)及灼烧感(2%);术后慢性痛的最强预测因素是术后第2天的疼痛强度。年发表一项荟萃分析及发表的一项回顾性研究均表明,目前疼痛处理方案并不能有效缓解术后急性疼痛。
目前,外科手术从住院模式转为门诊手术,并正向办公室手术转变。美国择期门诊手术中17%~24%在医生办公室进行。在这种形式下,疼痛管理不足成为门诊手术和办公室手术的最大不良预后,办公室手术也存在疼痛管理不足。
术后慢性疼痛的定义为术后持续3~6个月的不良感受和情绪体验,常存在神经病理性因素,其危险因素分为患者相关及手术操作相关,其中,术后严重疼痛是最大的危险因素。术后慢性疼痛的发生与生存质量下降、卫生资源负担增加等不良预后相关。此外,临床研究表明,术后慢性疼痛的发病在住院患者中非常普遍,也见于门诊手术患者。年发表于《临床疼痛杂志》(TheClinicalJournalofPain)的研究表明,门诊手术后慢性疼痛唯一有统计学意义的预测因素即为术后急性疼痛。
儿童也可出现术后慢性疼痛。年发表于《疼痛学杂志》的系统综述分析了四项研究,涉及各种手术类型,共计例儿童(6~18岁),术后12个月慢性疼痛发病率中位数为20%。与术后慢性疼痛相关的术前因素包括术前疼痛强度、儿童焦虑程度、儿童疼痛应对效能及父母疼痛灾难化,而生物学因素与医疗因素并不与之相关。此外,儿童术后疼痛存在两种特殊模式:①早期恢复,术后疼痛逐渐减轻;②晚期恢复,术后2周仍然明显。晚期恢复与父母疼痛灾难化相关,与儿童疼痛灾难化无关。
术后慢性疼痛的危险因素分为基因与患者相关性、术后急性疼痛、术中危险因子,以及生理因素四大方面。灾难化(catastrophizing)是指夸大的负性心理情绪,是多维度认知构想,含有“扩大”、“复想”和“无助感”三种成分。急性疼痛向慢性疼痛的转化过程包括手术引起炎症反应、周围伤害性纤维一过性激活、周围伤害性纤维持续性激活(敏感化),以及中枢神经系统重塑引起过度激活(结构性重塑)。
挑战2:术后呼吸抑制
以使用纳曲酮、通气量过低或O2饱和度低作为呼吸抑制预测指标,大手术后呼吸抑制发病率分别为0.3%、1.1%和17%。术后呼吸抑制甚至可见于患者自控镇痛(PCA)。大多严重呼吸抑制发生于术后第一个24小时。年发表于《外科学年鉴》(AnnalsofSurgery)的队列研究分析择期大手术后院内阿片过量的预测因素,该研究表明,药物滥用史是阿片类药物过量的最强预测因素,超过60岁人群的阿片类过量率更高,阿片类过量会增加院内死亡率、延长住院时间、增加住院费用。
应对策略:多模式镇痛
在保证术中及术后有效镇痛的前提下,将阿片类药物的副作用最小化,是临床上的一大困境。长效阿片类药物是指可使血药浓度持续超过最低有效阈值,理论上讲,比反复使用短效阿片药物更能有效缓解疼痛,后者的血药浓度在有效阈值上下波动。应根据起效及失效时间理性选择阿片类药物的使用。
多模式镇痛主要依赖药物药效学相互作用(受体水平或受体后水平),而非药代学相互作用(药物浓度变化),其目标在于降低毒性的同时辅助镇痛(两种药效相加等于各自药效总和),或仅在增加毒性的同时协同镇痛(两种药效相加超过各自药效的总和)。临床研究对药物联用的评估应同时评价镇痛效果及所有相关并发症。
年《麻醉学》杂志发表的《围术期急性疼痛管理指南》指出:麻醉科医生应尽可能使用多模式镇痛;患者术前准备应将术前给药作为多模式镇痛的一部分;除非有禁忌证,所有患者均应全天使用非甾体类抗炎药(NSAIDs)、昔布类(COXIBs)和/或对乙酰氨基酚。
杜冬萍教授:超声引导下一些疼痛治疗失败的困惑杜冬萍教授
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疼痛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
上海交通医院疼痛科
背景知识
三叉神经由眼支(第一支V1)、上颌支(第二支V2)和下颌支(第三支V3)汇合而成,分别支配眼裂以上、眼裂和口裂之间、口裂以下的感觉和咀嚼肌收缩。三叉神经痛就是大家所说的“脸痛”,一般发生在面部,它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神经内、外科病,这种病的特点是:在人体的头面部三叉神经分布区域内,发病骤发,闪电样、烧灼样、难以忍受的剧烈性疼痛。
超声引导下的神经阻滞对治疗很多慢性疼痛的治疗具有重大意义,如头面部疼痛、盆腔痛、截肢和幻肢痛等。在头面部不典型疼痛诊疗中,医院率先开展的经翼颚窝阻滞上颌支神经技术,在经过不断改进优化后,已取得令人满意的疗效。
经翼颚窝V2阻滞技术的发现
以医院年诊治的患者为例,该患者为55岁的中年女性,3年以来出现间歇性鼻唇沟疼痛(V2支配区域痛),多次行眶下神经阻滞无效,服用卡马西平mg/天,效果不佳,疼痛影响其正常工作和生活。
为解决患者难题,杜冬萍教授的研究团队查阅了相关文献,发现了使用超声引导下经翼颚窝阻滞V2神经的疗法。翼外侧肌和上颌动脉是超声引导下经翼颚窝阻滞V2神经的重要解剖标志。治疗时,患者取侧卧位,在超声探头与颧沟平行处下针,注药后患者当即感到上唇麻木,提示穿刺位置合适。麻醉科医生在该患者身上进行了首次尝试,令人欣喜的是,在经过2次治疗后,该患者面部不典型面痛得到了完全缓解。
经翼颚窝V2阻滞技术的优化
然而,该方法在施行过程中仍出现了大量效果不佳的情况。有患者在行颅内减压、γ刀术后复发不典型面部疼痛,多次神经阻滞后,效果逐渐变差,用药量也越来越大;有患者多次神经阻滞后疼痛有所缓解,但上唇没有明显的麻木;更有3例舌头麻木而上唇却未麻木的情况出现。这些失败的案例提示我们目前的经翼颚窝阻滞V2神经的疗法仍有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优化。
在整个科室的共同努力下,该研究团队带着探索的精神,再次查阅相关文献,并针对翼颚窝结构区域在人体标本上进行了大量的解剖学实验。结果发现,优化前的阻滞方法存在明显的缺陷。在解剖结构上,上颌动脉只在末段与上颌神经伴行,而之前的定位是根据上颌神经的中段来引导进针,穿刺针只到达了冠突后的颞下窝,并没有真正的到达翼颚窝,在颞下窝内阻滞剂朝后扩散浸润肌肉组织内额结缔组织,引发“上颌不麻下颌麻”的怪像。真正翼颚窝需穿过韧带,到达更深的解剖位置,方向更加偏斜向上。于是杜冬萍教授的研究团队真正发现了翼颚窝的超声定位,解决了这一亟待解决的临床难题。
经翼颚窝V2阻滞的启示
经翼颚窝V2阻滞必须首先在传统CT机下定位明确后,才能在超声引导下穿过上层韧带,到达翼颚窝阻滞上颌神经,需时时观察超声定位确定好解剖位置,才能达到最佳诊疗效果。很多时候文献中的记载也会存在偏差,需要我们自身积极探索发现事实真理。
简志诚教授:以临床指引为标竿的住院医师规培于台湾的推动简志诚教授
台湾麻醉医学会主席
医院副院长
台湾麻醉医学会的目标与策略
简志诚主席在任期间着重五方面工作:①明确提出台湾麻醉医学会的主张,依职权专业化分工;②强化专业以巩固专业权,编订相关标准或临床指南;③加强会员联系以形成有效共识;④住院医师教育结合临床指南以打造专业能力;⑤结合世界潮流与医学会一起努力,让学会持续与世界一起进步。
世界住院医师培训思维
传统教学模式由老师决定教学内容,通过考核评估教学效果。能力本位医学教育(CBME)是医学教育新典范,根据患者及医疗系统需求,明确麻醉专业主张及临床指南,以麻醉专业品质为考核评估水准,制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课程,体现了回应公众的教学模式。
美国研究生医学教育认证委员会(ACGME)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精神强调了里程碑式(Milestones)的培训及临床学习环境评估(CLER)。其中,麻醉学培训要求包括培训机构、人员与资源、住院医师培训周期、教育计划、评估体系,及学习和工作责任事件六大方面。ACGMEmilestone项目将各方面技能分为多个层次(Level),其中,能力评估分为五个层次:新手(Level1),已完成麻醉学计划的一年培训;高级初学者(Level2),尚不具备麻醉学亚专科的重要经验;合格(Level3),具有麻醉学亚专科经验;高级(Level4),可逐渐独立操作;专业(Level5),该医师已超过规范化培训确定的培训目标。该项目共包括六大方面资格,25个分支资格以及个“里程碑”,其培训方式倡导简化论,对于受训医师来说,可明确培训目标、反馈需进一步学习的具体方向、早期识别表现欠佳者、满足表现超常者的更高目标;对教学来说,利于教学计划改善、明确资格鉴定要求,早期识别表现欠佳者;对于公众来说,可更好识别某医师能胜任的工作,解释浅显易懂,可作为委员会认定依据。该模式也存在简化的各组分并不能完全反应整体技能水平,以及过于复杂、不易日常运用等缺点。
欧洲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提出可信任的专业活动(EPAs),是指某医师在某种情况下可被信任能够独立完成的必需操作。关键问题在于,能否信任该受训者可完成一项EPA。为此,其将EPA分为五个层次:①观察但不可操作;②可在直接指导下操作;③存在反应性指导下可进行操作;④远距离监督和/或事后监管;⑤可对其他初级者进行监督。
简志诚教授提出,应学习美国及欧洲培训思维,进行整合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利用EPAs进行培训,通过milestone进行评估。
台湾临床麻醉指南的制定及住院医师培训现状
台湾临床麻醉指南审定委员会参考各国临床指南制定了自己的临床指南,可使大多数麻醉专科医师顺利遵守,能外化为培训计划,培医院遵从,医院之间培训内容与评估的有效性一致,目的在于保证住院医师得到最好的培训。
台湾麻醉医学会milestone/EPA工作小组邀请全台湾约30位的麻醉医学专家进行3至4轮的Delphi问卷,问卷数据汇整完成本土化的Milestone评量表,以Delphi评估方式进行翻译、增修与重置,根据结果达成共识。召开专家会议,设计麻醉专科EPAs,将其与Milestones整合后,成为全新评核工具,针对设所计出的EPAs/milestones进行Delphi问卷。此外,利用谷歌文档使其无纸化、日常化,以数据分析对住院医师教学回馈于调整,使milestone数据化。
简志诚教授强调,住院医师培训的挑战在于,专科缺乏明确临床指南、培训计划与临床指南不相符、医院的培训计划遵从性参差不齐、培训内容与评估有效性并不一致,以及现行住院医师评鉴并不保证好的住院医师培训等,但是,以上也正是可以提高和完善的契机所在,是麻醉同仁一起努力的方向!
刘前进教授:床旁凝血功能监测和输血的结局刘前进教授
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
美国麻醉医师认证会诊医师
不可控的出血
一篇于年发表在《创伤杂志》(TheJournalofTrauma)的文章表明,创伤发生不可控出血的概率最高,为30%~40%,其次是心血管术后,于年发表在《麻醉与镇痛》(Anesthesia&Analgesia)的一篇研究表明,其不可控的出血发生率为5%~7%。
年发表于《胸外科年鉴》(TheAnnalsofThoracicSurgery)的文章对大出血的定义如下:术后24小时内,失血量>2L(成人),或急性失血量/患者体重>30ml/kg(小儿),或急性失血量>40%~50%血液总量。而对于老年人的大出血,更多的是外科或者血管组分问题,需要通过手术或者栓塞来进行干预。
年发表于《TheAnnalsofThoracicSurgery》的一篇文章揭示了发生不可控出血的相关因素,分为如下两部分:①患者相关因素,如老年、体型、性别、术前贫血、抗血小板及抗凝药的使用、低体温、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以及各种并发症(如充血性心衰、高血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外周血管病、糖尿病、肾衰等)。②手术相关因素,如长程手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创伤、创面出血以及手术水平等。
年发表于《TheAnnalsofThoracicSurgery》和年发表于《麻醉学》(Anesthesiology)的两篇文章揭示了发生不可控出血的危险因素:①患者长时间服用抗凝血药及氯吡格雷;②患者再次行手术治疗、肿瘤手术、主动脉手术、心脏手术、神经外科手术、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等;③透析患者;④创伤患者。
止血程度
年发表于《中华血液学杂志》(SeminarsinHematology)的一项研究表明,创伤、大手术以及血友病可能由于引起出血而导致死亡,但止血过度将导致中风、心肌梗塞及栓塞,引起凝血,同样将会导致患者死亡。所以说“止血就是生命的平衡过程”,但是在什么情况下要止血,止到什么程度,仍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TEG与ROTEM
凝血过程是各种血液成分相互作用,共同参与的一个过程,凝血的过程也是纤维蛋白溶解的过程。我们人为地把参与其中的凝血因子分为外源性和内源性,但事实上,这两种是区分不开的。如今,床旁血浆凝血酶原时间(PT)和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的检测被广泛应用,然而,仅仅知道凝血过程一种组分的改变不足以判断整个血液系统的凝集状态。年发表于《Anesthesia&Analgesia》的一篇文章介绍了三种临床上用于检测患者凝血状态的机器:TEG、ROTEM以及Sonoclot。根据原理来说,三者都是根据凝血过程,从最初的血细胞聚集、纤维蛋白聚集到血小板黏附最后启动纤溶过程,获得血栓弹力图进行分析。如今,TEG已被广泛应用,但是ROTEM作为一种新型机器,和TEG还是有很多区别和优势。
区别 ①转轴不同:TEM为杯转,ROTEM为轴转。与TEM相比,ROTEM更加的稳定方便且更加敏感;②ROTEM有4个通道,可结合临床情况对得到的血栓弹力图进行校正,从而得到凝血状态的真实情况;③ROTEM的A5、A10能够更加敏感快速地反映出患者的凝血状态;④ROTEM能够直接反映纤维蛋白原的水平并辨别纤维蛋白原或者血小板的减少。
优势 于年9月及年发表于《Anesthesiology》的两项研究表明,使用ROTEM降低了手术患者的出血量及输注血制品的量,并在改善患者预后方面也有一定作用。另一项年发表于《血液学》(Blood)的研究表明,ROTEM对于及时发现并纠正产后出血具有指导意义。
年发表于《麻醉学》(Anaesthesia)的一项荟萃(Meta)分析表明,与TEG相比,ROTEM能够更好地反映患者的血液状态,改善预后。年10月发表于《神经外伤杂志》(JournalofNeurotrauma)的一项研究表明,ROTEM能够更加快速地检验患者的凝血状态。
现有证据表明,ROTEM能够对于凝血过程的整体进行评估,并能够快速出结果从而改善预后,降低成本。但是ROTEM的检测过程是建立在理想化的基础上,不考虑温度、pH值等因素,它能否正确反映体内的凝血状态仍需要进一步探究。目前为止,关于ROTEM应用的循证医学缺乏高质量的临床试验,其检验结果还需结合临床状况进行专业评估。
敬请期待
第七届东方麻醉与围术期医学会议
(OCAP)
时间:年6月22-24日
地点:上海国际会议中心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