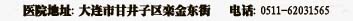我像一条沉默的土狗,闻遍了严塆的每一个角落——题记
(封面插图:《严肃作文》御用涂鸦师、大学同学邱赛强)
一
记录的真实,拒绝为尊者讳、为逝者讳。严塆人的诨名,上溯三代,从自家说起,由亲及疏,先近后远,倘若其他被记录者有所不悦,也就罢了吧。
我的诨名,叫“日本矮子”。不仅颇有些文化含量,还包含了对倭寇的国恨家仇。
这诨名,是我大哥给取的,念起来还有说唱艺术样式Rap风——“猴儿头,凹儿脸,大蒜鼻子三角眼,矮脚南特臭大蒜,日本矮子咚嘀咚。”
除了“矮脚南特”起语助词作用,大哥对他这个弟弟体貌的描述,十分准确。矮脚南特,籼型常规水稻,当年长江中游农村广种的稻种之一。
这也成为此后十多年,我自卑的唯一源头。
母亲也有个诨名,叫“温热儿”。母亲算是小家碧玉,年前,跟教私塾的嘎(ga)爹(外公)读过私塾,年后跟教扫盲班的嘎爹读过夜校。孩童时,白天缠足,遮人耳目,晚上被奶奶心疼,松了绑,半是天足。因是长女,被外公视为掌上明珠,家规严格,出阁前,除了学些女红,甚少出门,更遑论农事。
行为动静,慢条斯理,落下个慢性子,落了个“温热儿”的诨名。
我奶,个子高,塆里人称“长子二奶”,姑且算是诨名之一。奶的姑且算作诨名之二的,是近日塆里的发小严利军提供的。
塆里曾有顺口溜曰:“吴儿不惹,安儿不沾,惹到了杨儿(羊儿)叫翻了天。”说的是当年在严塆,最有狠的三个女老头儿,没哪个敢惹的。
“吴儿”,我叫八妈,用作第三人称时叫“吴儿八妈”,九十多岁寿终内寝,不算诨名。在八妈屋的北岸下,我捡过不少不知道哪家的、不在自家鸡帱生蛋的鸡的蛋。
“安儿”,队长花平哥的妈、利军的奶,安姓,我叫她二妈。也算不得诨名,她老人家的诨名,我在后头会写到。对这位二妈的记忆,是出现在自家屋门口,一脸严肃,叫我等在她屋门口的上塘,钓不得鱼儿,更脱不得裤头儿下水洗澡儿。因为地势,上塘也叫“岗儿塘”,是严塆的第一饮用水源。一直是花平哥家守着。花平哥去世后,岗儿塘就荒了,成了严塆主要的四口塘中,最脏的。
“杨儿”,就是我奶,杨姓,名讳“桂花”。在这个顺口溜里,谐音的“羊儿”,勉强算是诨名。
至于说,这三个女老头儿是严塆最有狠的,在我的记忆力,除了坐立行走有些威仪,别无佐证。
利军还说:“塆里老辈儿的男老头儿、女老头儿,都有诨名啊。”我觉得,这可能有些夸张。
(我细娘儿,婶,诨名“杨瘌子”,漂亮而腻害)
二
我叔伯的二伯,诨名叫“麻麻亮儿”。
是我大爹大奶的九个子女中的次子。因为家贫,二伯被父母安排务农,先是扶持我大爸严勉先生读书,接着扶持几个叔叔读书。一辈子,总是天不亮就起床下地种田,得了个“麻麻亮儿”的诨名。天要亮未亮时刻,老家叫“麻麻亮儿”。
二妈王姓,第三人称也叫“王二妈”,同辈或长辈,叫她“王儿”。大爹大奶家,在家的几房儿很晚才分家,几代同堂很多年。大房的一家在外工作,二妈统揽这一大家族的家务很多年。二妈修长白净,很好看的瓜子脸,说话走路轻悄了的,完全不像管家。二伯寿终正寝时,享年九十多。
六爷(叔),当过大队和公社书记,很讲革命原则,性耿,诨名“老嘿(he)”。“嘿”,方言音he,我感觉,有“憨”和“狠”或“轴”两层意思。六爷的诨名“老嘿”,应该指的是“狠”或“轴”。
作为“憨”的意思的“嘿”,很好理解。严塆就有叫“嘿头细爹”“嘿头细伯”的,这里的“嘿”,便是“憨”无疑。
我未出五服的堂姐严国光、“光儿姐”,是我叔伯三伯的细女儿,诨名“菜瓜”。大眼睛,漂亮,幽默,有善于自嘲的开朗。但个子小巧,多愁善感,也许还性情柔弱。觉得“菜瓜”,便是说她的性格。
几年,应该是夏天,光儿姐落到塆东头的河里去过一次,被人救了。有说是轻生,以我道听途说的模糊的信息,我当时是信的。但后来听说,光儿姐醒了后,说不是,是失脚了。
她大我四岁左右吧。很喜欢她。每次回湾里,都要去她家,先不打招呼,远远地喊“光儿姐光儿姐”。渴了要水喝,饿了要吃的,走的时候,土鸡蛋、落生儿、苕,或者新米,总要带一样两样。
还有个未出五服的堂妹,漂亮而紫版(ziban),因为儿时体弱,出工做生活(松糊)少些,诨名“冰棒”,意思是见太阳就化。紫版(ziban),浠水常用方言,不知两字写法,多指女伢性情沉静、温顺,知礼节。
父亲的弟弟、我爷(叔),诨名“壳儿”,不当面时,我们也叫“壳儿爷”。壳儿,或干壳儿,泛指病弱、干巴、黑瘦之人。壳儿爷成年前是“干壳儿”。
我细娘儿(婶),姓杨,名腊珍,身体好,漂亮,泼辣,伶牙俐齿,诨名“杨瘌子”。
作为昆虫的杨瘌子,丛(松)树上或林下,多褐色,统称毛虫;木子树(乌桕树)上或树下,多五彩缤纷的,专名杨瘌子。都沾不得,沾上了,痛痒无比。
(大夜壶、细夜壶,都是夜壶)
三
跟生理有关的诨名,我的“日本矮子”之外,还有一些。
次尧叔,长身大力,比例使然,脸自然也长些,得了个“马脸”的诨名。
我叫七姐的大儿、诨名“花脸”的,因为同时还有个诨名叫“干壳儿”,就有了“花脸干壳儿”这第三个诨名。“花脸干壳儿”大我三两岁,人很老实勤快,无非是脸上有一大片赭色胎记。
国义的小名,叫“掇儿”,头有顽癣,小时候被人叫了多年的“癞痢头”。当年条件差,尤其夏天,赤脚下田下地,头上长疮、脚上流脓的细伢,多得很。
新水我当面叫哥,背后也叫他诨名“三麻子”。现在想来,我是不曾从他脸上见过麻子的。不问究竟,只是跟着喊。
新中是七爹的儿,70年代初招工到了武钢,不过因为头大一些,诨名就叫“大头忠儿”,倒也不算歧视。我记得也当面喊过他“大头忠儿叔”,并不担心见怪。
新祥是新中的弟弟么?诨名“细眼睛”。无甚创意。
但“大眼睛”明哥这诨名,就是褒义了。大眼睛明哥是剃头的,也叫“待招”,老家话“招”,念轻声,听起来像是“者”,我就以为是“待者”。
“待招”的叫法,原来很有来历。连秃驴鲁和尚都会用,我都不晓得。
网上说,汉代以才技征召士人,使随时听候皇帝的诏令,谓之待诏,其特别优异者待诏金马门,以备顾问。唐初,置翰林院,凡文辞经学之士及医卜等有专长者,均待诏值日于翰林院,给以粮米,使待诏命,有画待诏、医待诏等。宋、元时期尊称手艺工人为待诏,即由于此。唐玄宗时遂以名官,称翰林待诏,掌批答四方表疏,文章应制等事。宋有翰林待诏,堂写书诏。辽有翰林画待诏。明清时,翰林院中仍置有待诏,掌校对章疏文史,但地位低微,秩从九品。
《水浒传》第四回:智深走到铁匠铺门前看时,见三个人打铁。智深道:“兀那待诏,有好钢铁么?”
明哥很斯文,剃头有风险。当年即便知道鲁和尚如此呼叫打铁的,也不会见了他,失礼地喊:“兀那待诏,有空儿剃头么?”
据说清时,满洲人的发型为“金钱鼠尾”式,即要把一个人的大部分头发都剃掉,然后留一小撮点扎小辫。为便于向百姓强制推行,清政府就组织起剃头匠来,这些人手持圣旨,归于待诏,享受俸禄,走街串巷,逮住一个剃一个。为此百姓便不叫他们“待诏”,而叫“逮住”。从此,串乡理发的都称“待诏”。
大眼睛明哥,负责一塆的头,是否也去隔壁塆,不知道。至于剃头的报酬,他的大女儿桂红最近联系上了我,说自她有记忆,一个头一年1块5角,后来长2块,慢慢地长,直到他最后不剃时,是50块钱一年。他应该是年,才撂了挑子,不剃的。
我记得当年,找明哥剃头,是有钱把钱,没钱就把鸡蛋顶。大蛋6分钱,细蛋5分。
有几个诨名,不知与生理有关,还是借物状人。
比如朱德元,我叫元哥的,诨名叫“大夜壶”。元哥是个壮汉,后自学厨艺,方圆十数里小有大名,曾被人请到海南做过厨子。
严友全,我叫叔的,诨名“细(小)夜壶”。因为觉得好玩,我只记得的另一个诨名,叫“尿半儿”。只是至今不知道,所指为何。
最不人道的诨名,是“浇公头”。这是严成武、我叫“成武哥”的诨名。成武哥聪明能干,很早就去了黄州印刷厂。貌似我的父亲,从中帮过忙。
浇公,是舀粪浇粪的工具,粗大毛竹一节(也有木制、浅桶状的),安一把木柄。所以叫“浇公”,大约用来浇菜浇庄稼,有功于人,窃以为是算是“尊称”。
农具中,被称为“公”的,就它一位了。不记得成武哥的头型,但“浇公”用到人头上,是很有些不堪的。
(“浇公”。窃以为是对粪瓢的尊称。找不到当年竹制或木制的“浇公”图片,这是塑料的。大异其趣)
四
涉及性格甚至品性的诨名,或借喻物件,尤其多借喻动物。
有诨名叫“锣鼓儿”的,我叫“锣鼓四妈”。好像是大眼睛明哥的婶,丈夫死得早,很多年是个“孤老头”,最后住进豹龙福利院,92岁寿终。
“锣鼓儿”,应该指四妈是个热闹人吧。
还有个对称的说法——“铜匠细爹、锣鼓细奶”,不知道这位“铜匠细爹”,是哪家的长辈,我如何称呼他。
诨名叫“炕坛细爹”的,此前已独立成篇,写过《跟“炕坛细爹”学打》,是雨生、雨林、雨柏的爹(爷爷)。不赘述。
经学大伯,诨名不好听,叫“劲棒”。据说指脾气暴,对人狠。是“三麻子”新水哥的父亲。棒,应该指“棍棒”,取“武器”“凶器”“暴力”之意。冠之以“劲”,显然是强调“厉害”。
借喻动物的诨名,比较生动。
发小严国和的伯(父亲),我叫“云中哥”,鹰鼻凹眼,力大,狠人。一家男丁似有西域血统。塆里人给他取的诨名,叫“癞鸡包”。癞蛤蟆,老家叫“癞鸡包”,据称碰不得,有毒。
利军帮我记起来几个诨名。
国富他伯、我叫仕成哥的,诨名“鸦雀儿”。雨清哥,诨名“鸦壳儿”。鸦,老家方言,其音,近似:厄啊切。“鸦雀儿”“鸦壳儿”,老家指的都是一种鸟儿,乌鸦。但这两个诨名,应该不是指不吉利,而是指说话随意、夸张甚至有吹嘘意。
估计是一个塆两个“鸦雀儿”,需要区别,又雨清哥年纪小些,只能屈就一下,叫“鸦壳儿”。
雨生他伯的诨名,叫“阴白蚁”,倘只涉及性格也罢了,望文生义,很容易还扯到品性,就比成武哥“浇公头”,还狠。
叫“狗子”的,严塆只有一个,其实不是诨名,是小名。因为在同龄人中辈分最高,被人“狗子”长、“狗子”短、“狗子叔”、“狗子爹(爷)”地叫多了,甚至快要忘了他的大名叫“严度”。
狗子是我发小、同学,论辈分,我要叫他“狗子叔”。
非关物件、也无关动物的诨名,还有:
发小、同学严南凯,读书很调皮,老师叫他“难改”。
发小南子他伯(父亲)、我叫炳林哥的,不知何故,诨名“奸臣”。
何姐的丈夫、建军她伯,我叫哥的,诨名“斋儿哥”,又诨名“老噎(ye)”。不知道是否信佛、吃过斋的缘故。“老ye”,不知何意,也不知写做“噎”还是“腌”。何姐很好人,每次回塆里遇见,都要扯着说几句话儿。
利军的奶,安姓,顺口溜里的“安儿不沾”,说的便是她老人家。诨名叫“霞(xia)器儿”。Xia器儿,似物非物,不知何物,老家比如“热闹”,但偏“咋呼”,也有“小喇叭”的意思。
与“霞”近音的,还有一种说法,叫“详快”,说快了,像是“霞(xia)快”,比喻人热情、大方、以助人为乐。
国泉他伯、我叫八爹的,诨名叫“刮器儿”。有“苕里苕气、嗝里嗝巴”、不太清楚的意思。
为解释“刮器儿”,利军还说了个故事:下塆有个三爹,书呆子,一天跟八爹搭咀儿,说兴的南瓜被亮光虫儿(萤火虫)噬了,问八爹见识。八爹就唬他:把南瓜扯了它,把亮光虫饿死它。结果,三爹真的回去,把南瓜扯了。
三爹也有诨名,叫“三驼子”。被严塆人公认读书读得最好的。民国时,考起过浠水县知府,因为回乡守孝三年,耽搁了就任。三爹成分高,也波及了下面几代人。
八爹的细哥七爹,人称“巧儿七爹”,心眼足,俏皮话多,人相与谈,多有跟不上他节奏的。
因为聪明而得诨名的,以严光大、我叫光大哥为最,叫“九个窟窿儿”。说人聪明,老家方言叫“有心扣”“心扣多”。心有九孔,怕是跟说湖北人是“九头鸟”、鸟有九头一样,比喻到极致了。
还记得“半天”这诨名。据说是因为德华哥的媳妇,做生活,总是出半天工。
(锣鼓儿)
五
至今我不明所以的浑名,也有三个。
下塆中段的继春,严塆的外姓,姓杨,她伯诨名叫“杨鼓子”,不知何意。一种铝制、桶状的厨具,烧水用,也拿来煮粥的器皿,老家叫“鼓子”。
我叫“土帝细爹儿”的,大名严子庸,成分似乎是恶霸。经常挨批斗,斗的多了,来去批斗场地中,总与塆里同姓的批斗者,一路说笑。土帝细爹大约终生并未娶妻生子,一直寡居。我还记得他住的那爿细屋,还不到一联。
他的弟弟,参加过抗美援朝,一直在山东工作和生活。为什么叫“土帝”,塆里似乎没人说得清楚。
湾里绰号叫“二升米”的,大名严崇礼,应该是“锣鼓儿四妈”的丈夫。早年在稻场保管屋当过保管员,估计“二升米”这绰号,与“升子”这种量器分口粮有关。古老的木制量器“升”,老家叫“升子”。
那个年代粮食紧张,队里的粮油棉花等都在保管屋,当保管员有权、舒服、工分也高。前后几个保管员,多是狠角色,要能六亲不认。“二升米”当保管员时,我家还在“打窠巴”——五个伢都冇长大,缺劳动力,母亲又不擅农事,有一次分口粮,他就指着母亲的鼻子骂过——“你么对得住这口粮哦!”
大哥记得他。说身高约1米6,龅牙,说话连珠炮,后来到楼上拿柴从梯上摔下,死时还五十岁不到。留下“锣鼓儿四妈”,成了个孤老头。
(左,升,老家叫“升子”。右,斗)
六
有些诨名,是伤心。
比如国全,在学校被叫“五保”。国容说,是因为他有病,体育课、劳动课都不参加。那是国全有一年搞“双抢”,下水洗澡儿滞病了后,得的诨名。
利军他伯、队长、花平哥,诨名叫“zha巴”。Zha,声调,去声。
老家所谓“zha巴”,具象的意思,指脏,如有眼屎,叫zha巴眼;引申义,指过日子不讲究,做事没条理。如家里凌乱,说“屋里好zha巴”;东西不值钱,统称“zha巴东西”,或特指“zha巴xx”;做事马虎或身上不卫生的,叫“zha巴人”。
也用作自嘲和自谦。端一碗吃的,遇人夸赞,自嘲说“zha巴东西啊”;来客捂饭吃,即便端出的是平日自己舍不得的东西,也会自谦“zha巴东西哈,莫谦啊,多吃点啊!”
网上有“皶巴”一词,应该接近这个诨名的写法:劳动汗出,又受风邪之气,风寒使汗孔突然闭塞,卫气不能外泄,郁在里边化热,迫使皮腠形成皶。皶,有皮肤上的渣的意思,即皮肤上的垃圾。
花平哥的诨名,就姑且写做“皶巴”吧。
伢一多,就家大口阔,大人就烦,诨名就来了。花平哥子女多,做奶的被噪的心烦,于是一个孙女就“鸡虱子”,孙子利军就“狗虱子”,最后两个孙子,大的“糠虱子”,小的“细虱子”。
花平哥上有二老,下有一窠子伢,又当了多年的队长,忙队里的事,叫他不“皶巴”也难。
除了“花脸干壳儿”,立文叔的诨名也是“干壳儿”。干壳儿,多是在困难时期产生的诨名、绰号。黑瘦,或者有病。这里的黑,指肉色不好,黄皮寡瘦。
严塆的“干壳儿”算是少的。小学同学秋天说,那时候,隔壁左右塆里,叫“干壳儿”的,黑糊了的。黑糊,浠水方言,极言其多。
我有个叔伯的爷(姑妈),大名严淑兰,诨名“半饱儿”。据说在塆里做姑儿时,遇人问“吃了冇?”她人老实,总是答曰:“半饱儿”。后来,不管是不是饭后,也有人开玩笑,这样问她、撩她。就为了听她回答一句“半饱儿”,一笑。
门口塘东边、连接上塆下塆的半坡上,住着雨平哥一家。在塆里,算是最穷的。多年来无数次地经过他屋门口,总觉一片寂静。
雨平哥有几个伢,不记得。只记得有个儿子尧生,诨名“大荒儿”,大荒儿有个妹儿,诨名“细(小)荒儿”。
大荒儿生于50年代末,名叫尧生,还是这几天问塆里人,才记起来的。但细荒儿的名字,甚至一时没问到。刚知道她跟我同年,完全没有同过学的印象,应该没读过书。
这兄妹两个的模样,我记得真切,都是“天怜相儿”,天怜人模样。
大哥说过一句话:大荒儿、细荒儿这两个诨名,完全是悲惨的象征。
(“鸦雀儿”“鸦壳儿”,老家指的都是一种鸟儿,乌鸦。)
●关于诨名
释义:指姓名以外的称呼,也称绰号、混号、诨号,它和别号、斋号的初级性区别,似在于几乎全部为他人所取,然后得到公认,使用性完全不取决于担当者本人的意愿。而任何一个绰号在获得多数人认可之前,又几乎全部是通过口耳相传的途径传播,这与别号、斋号的发生与流传照例都依赖文字自署、又多借助作品的方式,形成中级性区别。
基本概念:很多绰号都在与相貌、姓名、生理特征相结合的条件下,对担当者的禀赋德性、行为举止等作出外观与内涵有机统一的概括,同时富有强烈的公众舆论的褒贬性能,从而也在某种程度上构成社会评判机制的一个部分。它又和别号、斋号通为取用者个人思想感情的表述或纯主观性的自我评判和标示,形成高级性区别。
佛教释义:叫别人侮辱性绰号,为别人起侮辱性绰号者都属于造恶口业,首先为别人起侮辱性绰号者,罪孽更大,中国有句智慧名言,“始作俑者,其无后乎”造恶口业者会受到以下果报——如是恶口乐行多作。堕于地狱畜生饿鬼。若生人中。处处皆畏。一切人所。皆得衰恼。无人安慰。于自妻子。不得爱语。犹如野鹿畏一切人。远善知识。近恶知识。是名恶口三种果报。
起源:魏晋南北朝时代,士风丕变,读书人相互取用调侃性绰号陡增。
唐宋之文化氛围,益加开放流畅,世人互相品目、争取绰号是一种社会风气。
入元明后,诨名成为草莽文化和市井文化共同表象之一的特征业已定型。与此同时,在上流社会里,绰号又成为互相诋毁或派系斗争的一种工具。是为庙堂之高,江湖之远,绰号诨名,无处不传矣。
意义:绰号并非全是轻薄子之互相品目。有些绰号是公论所赠的美号。明代监察御史丁俊生活节俭,常食豆腐,人称“豆腐御史”;新繁知县胡寿安种菜自食,人称“菜知县”。明代荆州知府张宏,坚决不接待通关系走门路的人,时人赠号“闭门张”。
绰号又是讨伐邪恶、嘲讽奸佞的口诛之剑。如北魏人拓跋庆智任太尉主簿,不论大事小事,非贿不行,唯胃口不大,十钱起价,人“钱主簿”;还有不少文人骚客、书画高手或梨园名伶的绰号,多起于对他们学术和艺术成就的褒扬。如南朝刘孝谅,精通晋朝史实,绰号为“皮里晋书”;唐代李守素,最擅谱牒之学,绰号为“肉谱”;北宋词人张先(字子野)因平生有三句得意的词句皆带“影”字,被取绰号为“张三影”等。
从起用缘由看,绰号也可以作粗略分类,或描摹性情,或记述轶闻,或勾画相貌,或表述特长。而从语言艺术看,绰号对汉字文化潜力的开掘,在修辞手法上所达到的造诣,都远远超过了名讳、表字、别号、室名之类的平均水准。也许大多数绰号都不像前者那样或出于经典,或工于雕琢,缺乏书卷气雅致味,但它们运用简练精辟的语言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却真正能使担当者在人们闻见时而获得一种立体感。
绰号也有它的明显缺陷,有时或流入低级趣味,如讪笑他人生理缺陷,因比喻夸张而近乎为虐等。
嘿嘿
赞赏
人赞赏
北京哪家白癜风医院比较专业北京白癜风医院那家比较好